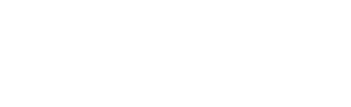[聯誼報]鈕守章:每一段歷史都是一個感人的故事
發布時間:2007-08-29 11:11:03
|
作者: 記者 林瑤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柳永的《望海潮》給人們勾畫出一幅富庶江南的美景,其中太湖南岸的湖州,則以“絲綢之府、魚米之鄉、文物之邦”成為江南的一顆明珠。湖州是世界絲綢文化發祥地之一,綢廠林立,創始于1918年的達昌綢廠,在湖州一直占有較重要的位置。作為達昌綢廠的繼承人、老一輩工商業者,原全國政協常委、省工商聯會長鈕守章先生給我們講述了屬于他的如煙往事。
肩負振興家門之重任 “我的事業,是在承繼父業中發展的。”鈕守章打開了記憶的閘門,深情地回憶著有關父親的點點滴滴。 鈕守章的父親鈕介臣,出生于1888年,是達昌綢廠的創始人。他21歲進湖州老惇泰縐紗莊,23歲被提升到上海老惇泰當會計。25歲那年,鑒于當時絲綢旺銷,生意好做,鈕介臣就離開老惇泰自己做縐紗行商,從湖州機坊販運縐紗到上海銷售。26歲起,鈕家兄弟三人與人合伙開設弘生昌綢莊,由行商轉為坐商,經營湖產綢縐運上海批發銷售,從而積累了進一步發展的資本。 1911年,鈕介臣兄弟三人開始在家里設置土法手工拋梭織綢機兩只進行家庭作坊生產,繼而增加到4只,名為“鈕達昌”,自產自銷。1918年,在小西街回龍橋合伙集資擴大了20臺人力織機。從此,湖州達昌廠漸漸興盛起來,鈕家也開始發達起來。 作為商人,鈕介臣總結出了一條“人無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廉”的生意經。民國初年,湖綢的主要原料是土絲,它是農村家庭土法繅制的絲。由于設備簡陋,絲的條紋粗細不勻、糙頭多、斷頭多,必須花人工復搖,而且產量低、質量次,不可能織造較細、較薄的高檔的真絲綢緞。為了力求產品向高、精發展,達昌綢廠決心自建絲廠,生產白廠絲織綢,1927年,鈕家在德清造起苕溪絲廠。然而抗日戰爭爆發后,日本為了在世界范圍和中國爭奪絲綢市場,有計劃、有目的地大肆破壞我國的蠶絲事業,他們的鐵蹄一踏上我江南沃土,見桑樹就砍,見蠶具就毀。苕溪絲廠就被日本侵略者拆機器、毀廠房,大肆搶掠了好幾次,偽軍土匪更是推波助瀾,趁火打劫,最后一把火燒光,瓦礫無存。 1946年,22歲的鈕守章剛從上海滬江大學的工商管理系畢業,人生的一次選擇擺在這位正直的年輕人面前。他本想出國求學深造,但是鈕介臣卻讓兒子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在這個兒子身上,鈕介臣寄托了太多的希望。 “其實我在念書的時候就已經到廠里實習了。在父親的管教下,我上午念書,下午到廠里管事,每天要寫匯報,工作很辛苦。”年輕的鈕守章并不像其他豪門少爺一般過得那么悠閑而輕松,嚴格的父親隨時都在提醒他要擔負起振興家門、振興產業的重任。“我父親會吸煙會喝酒,但是洋煙洋酒他從來不沾口,吸的是國產煙喝的國產酒。他對我們說的最多的是他當年當學徒時受的苦。”也許正是父親的言傳身教,因而鈕守章身上少了許多當時年輕人的奢靡習氣,如他父親一般節儉勤勉。 那時鈕家所擁有的絲廠、綢廠、煉染廠、面粉廠,廠子在湖州,管理處和銷售點在上海。年輕的鈕守章肩負父輩們的希冀和熱望,全身心投入到家族企業中,學到了不少企業運營知識和實踐經驗。他本以為可以學以致用,將自己所學到的專業知識,應用到實際工作中去,但事與愿違,國民黨腐敗統治所造成的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投機倒把替代了正常經營,正當的民族工商業者步履維艱、困難重重。動蕩的時局讓鈕守章很快陷入困境,從1946年到1949年解放,他苦苦支撐了3年,但鈕氏企業始終處于風雨飄搖之中。
被共產黨的兩件事感動 父親的選擇又一次影響了鈕守章。“解放戰爭初期,就有人勸我父親離開上海去海外,父親不為所動,立志留在大陸與企業共存。他對我說,他從小苦出身,一個鋪蓋到上海,什么苦都吃過,白手起家,沒干過壞事,共產黨如果要清算,他可以把所有企業奉獻給國家,個人還可以為國家繼續做工作。我父親還說,國外再好無非是流落他鄉受欺凌,國內再苦總是出生之地有根基。”至今,已過古稀之年的鈕守章,仍然十分敬佩父親的抉擇。 父親的執著給鈕守章樹立了信心,而他也從兩件親身經歷的事情上開始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看到了新中國的美好未來。第一件事是解放大軍進入上海市區那天,他親眼看到整整齊齊一排排露宿在南京路和金陵路行人道上的解放軍戰士。當時天下著細雨,經過日夜行軍,極度疲勞的戰士,寧可冒風寒,一個緊挨著一個露宿街頭睡得正香,很多商鋪的店主于心不忍,勸他們進屋去睡,但卻沒有一個戰士去驚擾老百姓。第二件事是解放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湖州市軍管會主任、市委書記、市長、總工會主席等領導來達昌綢廠和勞資雙方開會,會議開得很晚,結束時已經是萬家燈火,大家還餓著肚子,天又下著雨,幾位領導同志都沒有帶雨具,鈕守章要留他們吃飯,卻沒有留住。但見他們都脫了鞋,赤著腳,冒雨跑了回去。鈕守章在廠門口遠遠望著這些共產黨的“大官”們在雨中離去的背影,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他深信共產黨不僅能夠摧毀一個舊世界,也一定能夠建設好一個新世界。 事實印證了這一推測。1949年到1953年,受戰爭的影響,國內像絲綢之類高檔消費品的市場趨于萎縮,內銷非常困難,出口又被封鎖,有幾年外銷中斷,產品根本賣不出去,整個絲綢行業遭遇到非常大的打擊。“當時光鼓動恢復生產是沒有用的,因為生產的東西賣不出去,沒有錢買原料、也發不出工資,生產難以為繼。”此時此刻,經歷幾多風雨的鈕守章平和地說,絲毫看不出當時的焦慮、不安和不甘。然而當時的鈕守章幾乎是日不安、夜不眠,眼看父親交給他的家業危在旦夕,他卻一點辦法也沒有。就在他一籌莫展之際,政府開始收購它的成品、發放貸款,工廠也開始發工資,隨后外銷逐步通了,再采取加工訂貨等多種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扶持措施進行幫助,企業開始逐步好轉。 “我是真心感謝共產黨,感謝政府,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拉了我一把,為我帶來了春天的生機,要不然我父親創立的這份家業也許就……”鈕守章有些說不下去了。
積極投身公私合營 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鈕守章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工商業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其最高形式就是實行公私合營。1954年冬天,父親鈕介臣親自參加了湖州電廠公私合營后的第一次股東會,領到了分配的股息,他在公方代表的報告中聽到了公私合營后廠里的巨大變化,感慨地說:“我和李彥士(解放前湖州電氣公司總經理)打過官司,過去電廠的腐敗情形,我最清楚。我這個股東,從來沒有拿到過一分錢的股息,想不到共產黨短短幾年就把電廠搞得那么好,還發了股息,真了不起。”第二年公私合營達昌綢廠開股東會,他也參加了,使他驚訝和高興的是,公私合營后僅僅兩年,生產就大大提高。 說到公私合營,鈕守章回憶起1954年春夏之交時的一件事情來。當時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召開華東地區關于公私合營工作的座談會,在上海錦江飯店舉行。那時正值“黃梅天”,大水淹沒了湖州去上海的公路。去上海參加會議的代表、時任公私合營達昌絲廠私方副廠長的鈕守章,和湖州市委統戰部百友部長以及公私合營湖州電廠公方代表和私方廠長4人,只能從湖州乘劃船到江蘇盛澤,再上汽車,到上海已經是晚上八九點鐘了。原先準備在第二天作國家有關公私合營政策重要講話的上海市市長兼中共中央華東局副書記陳毅同志,因中央急召當晚必須趕赴北京,所以提前把講話錄好音,第二天華東地區工商界代表人士在座談會上聽到的是錄音講話。華東地區是我國工商業發達的地區,自然也是公私合營工作的重點,各省市工商界的代表人士齊聚上海共商國是,是一次很重要的會議,所以會期很長,開了十多天,除了聽取陳毅同志的重要講話以外,各地還介紹先走一步的公私合營企業的經驗和存在問題,并圍繞如何更好地推進這項工作(后來鈕守章才體會到這次會議是為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作準備的),發展生產,搞好公私共事關系,以及如何在進行企業改造的同時做好企業家的改造工作等等展開了討論。 “會上我遇到山東紡織業巨頭、大資本家苗海南先生,當時我還很年輕,不認識他,有人介紹才知道他解放前就去了香港,經中央和山東省委做了工作才回來不久。他為人正直,思想進步,積極擁護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開展社會主義改造的各項政策措施,我對他肅然起敬。我還記得他當時穿著筆挺全新的湖藍色中山裝,精力充沛,在會上還作了一個很好的發言,我很受啟發。”鈕守章的思緒穿越了時光,回憶著50多年前的生活片段。在會議中他與苗海南先生分在一個組討論,因為他的記錄比較全面,苗先生就向他借中央領導同志重要講話的記錄稿,準備抄寫,以備回去學習和傳達。鈕守章就給了他一份,他很高興,會議過后他們就沒有再見過面。 1955年冬,轟轟烈烈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在全國范圍內開始形成,中央和省市各級民建和工商聯“兩會”組織(民建是一個民主黨派,工商聯是一個工商企業的社會團體,由于他們的成員和工作對象多數是工商界人士,工作任務又基本相同,所以他們那時是合在一起辦公,簡稱“兩會”,直到1989年才正式分開)響應中共的號召,在中共各級黨委的領導下積極動員組織自己的成員,投入到這一高潮中來。作為先走一步的典型,在1954年就已經擔任公私合營達昌絲廠副廠長的鈕守章,更是興高采烈地走在工商界游行隊伍的前列,敲鑼打鼓迎接公私合營高潮的到來。最后廣大工商業者響應了黨的號召,無一例外地交出了生產資料,參加了公私合營,取得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 后來的20多年,是鈕守章人生的又一低谷,他被“莫須有”的罪名,被打成右派,最后按“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對他作出了“二類”處理。
見證香港湖州同鄉會的誕生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鈕守章的右派罪名,得到改正。1981年6月民建湖州市委會恢復活動后,他從絲廠被調到民建湖州市委會工作,1982年擔任了民建湖州市委會副主委,1986年任主委、民建浙江省委會副主委。1983年嘉興地區撤地建市后被選為湖州市第一屆和第二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對此,鈕守章動情地說:“我在政治上蒙受20多年的冤屈,我痛苦過,但是我沒有絲毫動搖過對黨的信念,因為我明白,世界上任何一個政黨、政府或其他政權組織,不論是資本主義性質的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都不可能不犯錯誤,關鍵是看它如何改正錯誤。我們常說我們的黨是偉大、英明、正確的黨,它之所以偉大、英明、正確,我認為就體現在這里。”
當時中央號召對外擴大開放,寧波、杭州、溫州等市走在了前列。湖州市委要積極聯絡在港澳臺僑中的湖籍人士(特別是其中的工商界人士),在他們中間擴大湖州的影響,市委統戰部動員鈕守章和民革湖州市委會李承威主委(已故)兩個人一起,用私人探親的名義赴香港進行聯絡活動,鈕守章欣然接受了這一光榮任務。父輩至交、姻伯倪坪蓀先生以87歲高齡,像對待自己的子侄一樣,為鈕守章的到訪作了周到的安排。在香港逗留的20多天時間里,在倪老先生的引薦下,鈕守章先后與同鄉親友接觸達100多人次。他們多數屬于工商界的中上層人物及新聞出版界和知識界著名人士,其中有怡和公司顧問顧乾麟,鈕守章的老同學、榮毅仁的堂弟香港南洋紗廠總經理榮鴻慶,香港書籍文具業同鄉會理事長、利通圖書公司總經理沈本瑛,寶豐保險公司總經理許惠源以及絲綢同行沈炳麟、沈善臣、沈善恂昆仲等。此外鈕守章還結識了很多新同鄉、新朋友包括他們的子女,他們中間有湖州陸家花園原來的主人陸心源的后代,現在香港、美國、毛里求斯設有十多家毛紡織廠的亞洲紡織集團陸增鏞、陸增祺昆仲;湖州著名書法家王一亭的曾孫王孝治、王孝行、王孝達、王孝方、王孝仁五位昆仲。
在接觸中,他了解到,湖州移居港澳的同胞,包括他們的子女不下2000人,但是他們中間在湖州有祖居、祖墳和親人、家屬、故友并經常回來的,不過幾百人,占少數,屬湖州籍但在湖州既無祖居、祖墳又無親屬、朋友,以及原籍湖州,后來移居上海,從上海再去港澳的,占多數。不管哪部分人,他們對故鄉湖州都有濃厚感情,他們都關心祖國的命運,更關心家鄉的興衰。但是他們畢竟長期生活在海外,對大陸的一切缺乏了解,加以處于不同的社會制度里,難免會產生一些不同的觀點,較普遍的是怕政策變,特別是一些從事工商業的人士怕在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以后對他們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等等。與此同時,港胞也反映了一些實際問題,例如落實私房騰退問題,要求在大陸的子女去接替在港父輩的事業問題等等。鈕守章回來以后都分別向政府有關部門作了反映,得到了支持并按政策規定逐步給予解決,受到港胞的擁戴。
在聯絡海外老一輩僑胞的時候,鈕守章發現還必須重視做好他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工作。老一輩人愛國愛鄉情誼比較深,但大多數年事已高,他們的第二代,許多人雖然在事業上有了一定成就,但家鄉觀念就不像前輩那么深,第三代則更是如此。他們中間有的甚至只知道自己的老祖宗是湖州人,卻不知道湖州在哪里。在接觸中,鈕守章還了解到,在香港的湖州籍同胞,他們也不是經常有機會相互接觸。因此他提出了在香港組織湖州同鄉會的建議,得到了在港湖州老鄉們的贊賞和支持。經過4個多月的積極籌備,1987年6月7日,在香港銅鑼灣珠城酒樓舉行了湖州香港同鄉會成立大會,倪坪蓀先生被推選出任首屆會長,香港文匯報、大公報、明報等均對此作了報道。此后在香港的報紙上經常能見到介紹湖州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的照片和文章,擴大了湖州在香港人士中間的影響。
當年6月25日,倪坪蓀老先生專程由香港來杭,向省和湖州市領導匯報同鄉會的籌建經過和今后打算,受到了省僑辦和湖州市委、市政府領導的熱情接待。顧乾麟先生于6月底率領由其父親叔蘋公命名的獎學金所培養的70余名學生,在湖州道場山叔蘋公墓地舉辦獎學金設立60周年紀念活動。香港大業制造公司沈炳麟先生除了在故鄉雙林鎮捐資建造公園、敬老院、中學科技館、小學教學樓,改造醫院住院部之外,又在湖州城區捐資建造福利院和碧浪湖亭榭等。和鈕守章有同鄉、同學、同年“三同”關系的香港亞非紡織集團總經理陸增鏞先生及兩個弟弟增祺、增鈺,以往跟內地很少交往,通過這次接觸才知道他們陸家與湖州有深厚的歷史淵源。
香港湖州同鄉會在港湖兩地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會務逐步取得進展。浙江省和湖州市多次去香港或在內地舉辦的各類經貿和聯誼活動,都得到了同鄉會的支持和幫助。首任會長倪坪蓀先生因年事已高,于1991年前回大陸定居,寓居上海,由其孫子、孫媳陪侍10多年,于2001年逝世,終年101歲。其長孫倪永平在香港經營的裕隆軸承設備公司已遷至廣州番禺,并在上海開了分廠。倪先生在上海定居的10年中,盡管鈕守章調離湖州,但出于“忘年交”的深厚感情,逢年過節,他總要專程去上海探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時刻。
感受湯老的真誠關心
1989年民建、工商聯分家后,因工作需要鈕守章調任省工商聯副會長,同時被選為第七、第八、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1997年任省工商聯會長,并被選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直到退休。
這一段歷史中,有個人給鈕守章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為調我到省里,時任省工商聯會長的湯元炳先生做了很多工作,多次向省委提出要求,調來之初,湯老要我把工作重心放到我兼任總經理的省工商經濟開發公司上。為了便于管好公司并節約開支,我放棄調配干部住新新飯店的待遇改住在公司頂層安家落戶,在盛夏時,頂層受日照強,特別熱,當時空調不普遍,白天受的熱,散不出去,要到很晚才能入睡。湯老十分關心,派人送西瓜到公司五樓給我消暑,甚至把他自己的煤氣罐送給我用。”時間過去了將
近20年,鈕守章依然清楚記得那感人的一幕:一個細雨迷蒙的夜晚,湯老偕夫人張元和女士撐著雨傘,步行到公司上五樓來看望鈕守章,噓寒問暖。
生活上,湯老如親人長輩般關懷,但在思想上、政治上以及工作上,湯老又如嚴師,對鈕守章要求相當高。一次湯老對鈕守章說起他對一位即將上調中央的民主黨派領導同志的臨別贈言:“民主黨派同志的職務提升是黨的培養,組織上的安排,和工作需要所決定的。有本人自己努力的一面,但不能把職務的提升和自己現有的素質和水平劃等號而自滿起來。相反更應該正視自己的不足,努力克服,求得進步,才能真正在新的工作崗位上適應下來,才能不負眾望。”湯老把這番話講給鈕守章聽,實際上是對鈕守章的一次教育。時隔多年,至今聲聲在耳,記憶猶新,難以忘懷,使鈕守章終身受用不盡。
黨重視和關心個私經濟的健康發展,在對待發展中的個私經濟的提法上就可以看出,從開始把它作為公有制經濟的“有益補充”到“必要補充”,從“組成部分”到“重要部分”,再到1998年把它寫進憲法;個私經濟企業主由原來的不允許入黨到允許入黨,以及確立私有財產權,和給予他們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光榮稱號等,都作了規定,從政治上、法律上明確了個私經濟的地位,這是時代的要求,社會的進步。
鈕守章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期間,曾接受過英國BBC廣播電視公司記者的單獨采訪。記者問,解放初,你帶頭申請公私合營,把企業交給國家,而現在又積極支持國家發展個私經濟,有什么想法?還有就是國家鼓勵個私企業發展的政策今后會不會變?對于第一個問題,鈕守章覺得應看到黨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歷史使命。新中國甫一成立,國家要展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首先自身要有一個強大的國民經濟基礎。如果不對當時存在的大量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國家就不可能在較短時間里開展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恢復國民經濟,也就不可能出現今天這樣繁榮富強的局面。只有我們的國民經濟強大了,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了,才有可能提出“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題,發展多種經濟成分”的政策來推進我國的經濟建設向更高層次發展。至于第二個“政策會不會變”的問題,鈕守章認為只要這個政策有利于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國家綜合國力的增強,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誰也改變不了它,在這方面是可以堅定信心的。
向江總書記當面匯報
鈕守章深深地記得發生在2001年3月4日上午的一幕:全國政協九屆四次會議期間,當得知江澤民總書記要親自到民建和工商聯界別聯組會議上參加討論,鈕守章精心準備就工商聯在組建自己的行業協會和同業公會過程中所遇到困難的發言。當時民建和工商聯各有4名委員發言,輪到鈕守章發言,因時間已近11時,主持人希望留些時間讓總書記講,不再安排發言了。總書記看了一下名單,親切地說:“我的講話不長,還是請浙江的鈕守章發言吧,他講同業公會問題。”總書記點了名,鈕守章就講了,他說工商聯辦同業公會是有歷史性的,但現在卻沒有被民政部列上主管部門,這是說不過去的,現在搞市場經濟,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從現實上,工商聯組建自己的同業公會作為工作的載體是必須的。總書記插話說:“說到工商聯辦同業公會、行業商會的確有歷史性,那個時候我在上海當一個食品廠的廠長,上海的同業公會非常厲害,他們搞行業自律,行業團結合作很起作用……當前國家正在搞機構改革,有很多事情正在發展過程中。工商聯辦同業公會這個問題雖然我們還沒有商量,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應該發揮各自的優勢,工商聯組建自己的同業公會是必需的。”江總書記還非常關心工商聯的工作,提出了“三個結合”:第一要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把自身企業的發展同國家的發展結合起來;第二把個人的富裕同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第三把遵循市場經濟法則和發揮社會主義道德結合起來。
鈕守章深切地知道,這三個結合,是黨和國家對工商聯的殷切期望,是工商聯開展工作的重要指導方針。作為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經濟的助手,工商聯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就是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健康成長和企業的健康發展,想他們之所想,急他們之所急,為他們服務,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維護職工的具體利益。
(本網站注:鈕守章曾擔任民建浙江省委會副主委、湖州市委會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