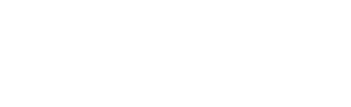永久的懷念——記唐巽澤幾件事
發布時間:2010-05-12 16:29:18
|
作者: 原民建浙江省委會副秘書長 周平英
唐巽澤(1911---1968),湖南湘潭人,原名唐永濟。1949年參加民建,1950年發起籌建民建杭州分會,1954年負責籌建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歷任民建杭州分會主任委員,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民建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委員、民建中央常委。解放后,任杭州市工商聯籌委會副主任委員,第一、二屆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和協商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浙江省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委員,浙江省水產廳廳長,省政協副秘書長、副主席。
2005年是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60周年,又是民建杭州市委會成立55周年,民建浙江省委會成立50周年。1950年,唐巽澤受民建中央委托負責民建杭州分會的籌建工作,1954年,又負責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的籌建工作,并先后任省、市民建主任委員。此時此刻,許多往事在腦海中縈回,其中一個瘦長的身影清晰地浮現在眼前,他就是我的愛人唐巽澤。
擁護國共合作抗日政策
1925年,巽澤在南洋大學(交大前身)附中讀書期間,受同學徐由整(中共黨員)的影響,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1927年被學校以亂黨分子的名義開除。1928年考入復旦大學政治經濟系。1931年冬以三年半修完四年的學分,提前半年畢業,獲學士學位及律師證書。
1932年在浙江省建設廳合作室工作,歷任課員、技士、科長等職。在職期間,他參與培訓合作基層工作人員,為浙江合作事業的開展打下了基礎。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2月杭州淪陷,浙江局勢岌岌可危。時任浙江省省長的黃紹■,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幫助下,贊同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決定在龍泉、遂昌、云和三縣建立浙江的抗日根據地,選派有愛國熱情、年輕有為者任縣長,巽澤被任命為龍泉縣縣長,時年28歲,是當時最年輕的縣長。
1938年1月,滿懷愛國熱情的他,帶同合作界一批青年同事,并通過徐由整邀請部分共產黨員同赴龍泉工作,當時到龍泉工作的共產黨員有邵荃麟、王朝聞、張三揚、舒文等。在龍泉,為適應抗戰形勢的需要,他改革了舊縣政府的許多陋規,如增設政治工作指導室(簡稱政工室)、戰事政治工作隊(簡稱政工隊)等部門。這些重要部門都由中共黨員負責,開展宣傳抗日救國活動,如辦起圖書室、閱覽室,其中陳列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斯諾的《西行漫記》等進步書刊,供大家閱讀,后雖被查禁,私下傳閱的人仍不少。還成立歌詠隊、話劇團,開辟宣傳欄,教唱抗戰歌曲,演出活報劇等。通過一系列活動,民眾的抗日熱情日益高漲,隨處都可聽到“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等歌聲;街頭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激發起了群眾對日寇和賣國賊的仇恨,增強了民眾對抗戰必勝的信心和決心。
在中共黨員的幫助下,巽澤還采取種種措施,如實行“二五減租”,減輕農民的負擔;以平抑糧價,幫助群眾組織生產等辦法解決人民生活困難。在征兵方面,不采用抓壯丁的方式,而是通過宣傳,動員青年自覺報名。在逢年過節時,邀請烈軍屬到縣政府聚餐,親自向他們敬酒,形成“烈軍屬光榮”的風氣,因此青年參軍踴躍。
龍泉抗日進步活動的蓬勃發展,得到進步人士的贊許,有人稱龍泉為“紅色的龍泉”,唐巽澤為“紅色縣長”,名記者曹聚仁在一篇報道中稱龍泉為“東南的堪察加”。與此同時也引起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極大恐慌,他們散布謠言說:“龍泉已成為‘蘇區’。”當地的地主豪紳們也因巽澤的各種措施侵害了他們的利益,對他恨之入骨,他們組織了“吃唐會”,以誣告、陷害等手段妄圖趕走唐巽澤和共產黨。他們先利用美人計把收發室的工作人員拉下水,要他銷毀往來文件,致使上下公文往來受阻,直到上級追查縣長責任時,才發現這是土豪劣紳們設下的陷阱,幸虧收發人員只將文件藏在地板下,未予銷毀。真相終于大白,但國民黨黨部仍借此事提出要改組縣政府。
土豪劣紳們一計未成,又生一計,他們利用縣自衛隊隊長吳玉坤喜歡吃喝嫖賭,以請吃、請賭把吳玉坤拉下水,吳輸光了積蓄、餉銀,最后竟盜賣槍支,土豪劣紳們抓住這點,威逼利誘,唆使他上山為匪。當吳帶領十幾個士兵攜械上山后,豪紳們立即散布說“唐巽澤的親信攜帶槍支投了共產黨”。一時間謠言紛起,國民黨黨部抓住這一機會要嚴辦唐巽澤,在這危急時刻,龍泉的共產黨組織動員所有黨員和政工隊員隨同縣政府追捕部隊一起上山,開展政治喊話,吳手下的士兵紛紛攜械歸來,最后吳被抓回槍決。事實搞清,但國民黨仍把“唐巽澤的親信自衛隊長吳玉坤攜帶槍支投奔共產黨,在多方的壓力下吳玉坤被追回槍決”作為“事實”記入檔案卷宗中。這也就是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貼出“揪出歷史反革命唐巽澤”的大字報的依據。
1939年,國民黨在抗日前線節節敗退,但反共氣焰更為囂張,龍泉的共產黨員處境日益惡化,為避免損失,黨組織將黨員陸續調走,有的去了抗日前線,有的到了革命根據地等,在黨員都走了以后,巽澤也被調回建設廳任合作管理處副處長。巽澤雖離開了龍泉,但當地老百姓卻一直把他銘記在心。記得1981年我參加省政協副主席彭瑞林組織的一次學習考察活動,在龍泉學習考察時,有幾位七八十歲的老人知道我是唐巽澤的妻子,便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開,嘴里不住地說:“唐縣長好、唐縣長好!”他們的舉動深深感動了我,使我對巽澤在龍泉的活動有了更多的了解。
被逼在滬尋求新的發展
1946年9月,我從遵義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復旦大學新設的合作系。上課時,經常聽到老師介紹浙江的合作事業,并稱贊浙江合作界的唐巽澤是個人才。老師多次的提及,給我留下較深的印象。次年暑假,我被分配到杭州在浙江省合作處下屬的一個單位實習,唐巽澤是合作管理處處長,因是校友,他對我比較關心,因此我與巽澤有了較多的接觸。當時因杭州公務員罷工,巽澤被國民黨省黨部懷疑為策劃者,對其施加壓力,巽澤被迫離杭去滬謀生。在上海的老同學的幫助下,他掛牌為律師,同時到復旦合作系兼課。
巽澤在復旦合作系講授的是合作運動史,他以社會發展史的觀點來講課,由于他的學識,他的口才,以及深入淺出、生動的講解,深得同學們的歡迎。他喜歡接近群眾,同學們也喜歡他,故在課前課后總有不少同學圍繞著他談論一些問題。他來上海后,使我對巽澤有了更深的了解,1948年我們終于結為伴侶。
在上海,巽澤有很多朋友,其中有共產黨員、民主人士以及從事其他職業的。他與他們接觸頻繁,通過黨員,他了解了共產黨在解放區的方針政策;在與民主人士的接觸中,他參加了民主革命同盟(又稱“小民革”);在與其他人士的交往中,他根據黨的方針政策采取適當的方式進行宣傳,特別是在1948年,解放軍南下勢如破竹,上海許多工商業者由于對黨的政策不了解,聽信謠言,人心惶惶,有想逃香港的,有準備抽資的,巽澤根據黨的政策以友情規勸他們,終于使他們以觀望的態度留在上海。
為勞軍工作不辭辛勞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我們親眼目睹解放軍軍紀嚴明,不進民居而露宿在馬路上,深受感動。“七一”前,巽澤接到杭州市軍管會的通知,邀請他參加“七一”民主人士座談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馬寅初、李士豪、姜震中、蔡一鳴等,會議由軍管會主任譚震林主持。巽澤在會上率先發言,贊揚共產黨的城市政策,并對恢復和發展生產提出了建議,引起譚震林等領導的注意。接著馬寅初又在會上贊揚了巽澤在龍泉的業績,稱他為“年輕有為,廉潔的縣長”。會后譚震林主席邀請巽澤回浙工作,他欣然同意。
回杭后,巽澤即參加由馬寅初主持的杭州慰勞解放軍總會的工作,擔任副組長并負責籌款事務。為了解放全中國,解放軍南下的任務很緊,勞軍工作非常緊張,他經常工作至深夜才回家。杭州解放不久,國民黨潛伏的特務不甘心失敗,妄圖以恫嚇、威脅,甚至寄附有子彈的信件,企圖阻止和破壞勞軍工作,但巽澤不為所動,堅持工作到勞軍總會結束。
在勞軍籌款期間,他與杭州工商界中的上層人士有了較多的接觸。7月,杭州市組織部分工商界代表人士赴華北、東北參觀訪問,巽澤任團長,在經過北京時,參加了民建。途中,他與工商業者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交往。回杭不久,就擔任了杭州市工商聯籌委會的副主委,負責宣教和日常工作,從此,與工商界結下了不解之緣。
籌建杭州民建,貫徹黨的團結教育改造方針
1950年6月,巽澤根據民建總會指示,負責籌建民建杭州分會。在籌建過程中,他通過工商聯的工作,動員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參加民建。當時工商業者對參加民建心存顧慮,主要是擔心萬一國民黨回來要吃苦頭,但在他的動員下,很多人還是參加了,我當時在做工商業者家屬的工作,也參加了民建。一年后,分會成立,會員人數已達數十人。
解放初期,巽澤根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對工商業者進行愛國守法教育,組織學習《共同綱領》、《過渡時期總路線》等。但由于工商業者認為共產黨要消滅階級,一定會利用各種機會來沒收資本家的財產,因此當“五反運動”開始,要工商業者交代“五毒”行為時,很多人怕交代多了今后拿不出,交代少了過不了關,顧慮重重,有人湊足資產數,作為交代的數字,認為政府把資產拿去,自己就可以摘掉資本家的帽子,不必再挨斗挨批。這種思想在工商業者中引起共鳴,思想一度比較混亂。巽澤發覺這一問題后,利用大會小會,反復講清黨的政策,使工商業者的思想逐步得到澄清。當時,有不少工商業者擔心被評為違法戶,但由于思想工作深入,嚴格按政策辦事,極大部分都被評為完全守法戶,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從此工商業者對黨的政策開始有所認識。他們說:“唐主委作報告深入淺出,聯系實際,針對我們的問題啟發性強,幫助我們解決了不少思想問題,掃清了思想障礙。”因此,凡民建、工商聯開大會,只要聽說是唐主委作報告,幾百人的禮堂就座無虛席。
1952年,巽澤參加第二批赴朝慰問團。在朝鮮,他接觸到的志愿軍都很年輕,并且憨掬可愛,對從祖國來的親人,他們給以熱情細致的照顧。在慰問中,他深深地被志愿軍戰士的英勇事跡和中朝人民血肉相連的情景所感動。他在回國后的傳達匯報中,以生動而充滿激情的敘述,報告了他在朝鮮戰場上的所見所聞,特別是在表達志愿軍戰士“為了祖國,前進!”的呼喚時,臺下的聽眾無不為志愿軍戰士為了保家衛國,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大無畏精神而動容,堅信抗美援朝必勝。
巽澤非常重視群眾工作,只要稍有空就會到基層去找幾個會員座談,傾聽他們對形勢、政策以及工作的看法和意見,他不僅身體力行,要求干部也如此,他說:“我們做群眾工作,不接近他們,不了解他們的想法,如何做好工作。”在他的帶動下,民建的干部和會員之間的感情是非常融洽的。省、市民建機關的干部不多,會員卻不少,每個干部至少聯系一個支部,每周一次支部組織生活,會前需開支委會,必要時還要到企業了解情況,為了適合會員的時間,支部組織生活都安排在晚上,其他許多會議也基本上都在晚上,因此會機關經常是燈火通明。干部不僅白天晚上需要工作,還要利用星期天到會員家中家訪。機關干部都習慣了這種生活,會員也樂于到會里來拉拉家常,談談思想,提提意見和建議,并及時將情況綜合報黨委部門,得到黨委部門重視。
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開始后不久,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自由民主黨要召開代表大會,邀請民建中央派代表參加。民建中央決定由副主委胡厥文出席,并要浙江的唐巽澤和天津的唐寶心陪同前往。巽澤是整風領導小組成員之一,接到這一通知后感到左右為難,去民主德國是民建中央對他的信任,但又擔心會影響“整風反右”工作。省委統戰部知道后,認為去民主德國的任務也是統戰工作,答應替他安排好工作,讓他安心去。到了民主德國后,可能由于路途疲勞,他發高燒,但仍堅持工作,當民主德國朋友與他握手時,才發現他在發燒,一定要他去醫院看病,當他瘦骨嶙峋的身軀暴露在醫師和民主德國朋友們的面前時,他們無不驚訝萬分,慨嘆說:“像唐這樣的人還在工作,真是不可思議。”他們無不感佩中國人的刻苦頑強精神。
巽澤對自我改造抓得很緊,平時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深入研究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對家人也不放松,一再告誡:“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放松改造就容易犯錯誤。”他的生活比較儉樸,上班、開會只要離家較近,他都不坐車,有人為他叫車,他說:“步行能鍛煉身體,步行慣了,沒有車也行。”在20世紀60年代的3年自然災害時,政府號召大種大養,我們利用屋前的一小塊園地,種上番茄和南瓜,收獲雖不多,讓孩子們也有了學習勞動的機會。
巽澤不僅在民建、工商聯擔任領導職務,他還是杭州市政府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省水產廳廳長及省政協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由于擔任的職務多,聯系的群眾面亦廣,為了無愧于擔任的職務,他總是盡可能地抽出更多的時間來做好各項工作。政協是各界人士和知識分子云集的地方,在知識分子中由于家庭出身不同,接受教育的途徑各異,因此對接受黨的領導和思想改造的認識,也有很大差異,擁護的有,抵觸的也不少,觀望的更多。為了端正大家的認識和態度,巽澤在政協的支持下,組織知識分子根據各個時期的中心展開辯論,在辯論中明辨是非,在自我教育中推動自我改造。知識分子對這種比較寬松又能夠敞開思想的辯論感到得益不少,很多人的態度逐步有了轉變。
由于巽澤過去的經歷,在浙江的愛國人士中彼此都有所了解,雖然各人經歷不同,但相互間比較信任,各項工作容易協調,為統一戰線工作的順利進行,發揮了作用。
冤假錯案終于平反昭雪
1966年5月,電臺廣播了“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消息,不久北京市委改組,巽澤有些震驚,其時他因心臟病休息在家。接著我家被抄,他被勒令掃街,這些他都不在意,認為運動難免有過激的行為。當宣布挖出“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并說這是統治17年的黑線時,他預感到一場政治風暴即將來臨,擔心身體是否能經受得住這場風暴的沖擊,我也為他而擔憂。
運動很快席卷了全國,民建、工商聯的造反派貼出了“揪出歷史反革命分子唐巽澤”的大字報,并聲稱要剝去他的“紅色縣長”及左派的兩張畫皮,在這正反錯位、是非顛倒的歲月里,他感到有口難辯。被勒令交代的同時,外調人員接踵而至,由于他過去接觸的人多,加上年代久遠,許多人和事已想不起、記不清,不能滿足外調人員的要求,因此受挨打、遭辱罵,幾成家常便飯,但他說:“我必須實事求是,我不能害人。”
在無休止的寫交代、寫外調材料的重壓下,本來就瘦弱的他,更顯得骨瘦如柴。長期的失眠,安眠藥從2片增到8片。1968年8月,我隨單位去嘉興“雙搶”,孩子們又有各自的活動,家中無人照料,他的身心遭受了雙重摧殘,尊嚴喪失殆盡,心力交瘁,高燒不退,終于無力承受,被逼含冤而死。但即使在他決心離世之際,還念念不忘教導家人“要聽黨的話,走社會主義道路”。
1978年9月19日在杭州舉行“唐巽澤先生追悼會”,為他恢復名譽。追悼會由省政協主席毛齊華主持,省政協副主席、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余紀一致悼詞。
悼詞中說:“在抗日戰爭初期,他擁護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贊同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在抗日戰爭期間做了有益的工作。全國解放后,他擁護、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周總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熱愛社會主義祖國,他努力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關心國家大事,歷次運動都積極響應,堅決貫徹執行我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多年來,他在我省工商界以及其他愛國人士中,做了大量工作。為鞏固和發展我省統一戰線工作貢獻了力量,是一位長期與我黨密切合作共事的老朋友。”黨為巽澤平反昭雪,他可以安息了!巽澤走了,留下的卻是我們對他永久的懷念。
2005年是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60周年,又是民建杭州市委會成立55周年,民建浙江省委會成立50周年。1950年,唐巽澤受民建中央委托負責民建杭州分會的籌建工作,1954年,又負責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的籌建工作,并先后任省、市民建主任委員。此時此刻,許多往事在腦海中縈回,其中一個瘦長的身影清晰地浮現在眼前,他就是我的愛人唐巽澤。
擁護國共合作抗日政策
1925年,巽澤在南洋大學(交大前身)附中讀書期間,受同學徐由整(中共黨員)的影響,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1927年被學校以亂黨分子的名義開除。1928年考入復旦大學政治經濟系。1931年冬以三年半修完四年的學分,提前半年畢業,獲學士學位及律師證書。
1932年在浙江省建設廳合作室工作,歷任課員、技士、科長等職。在職期間,他參與培訓合作基層工作人員,為浙江合作事業的開展打下了基礎。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2月杭州淪陷,浙江局勢岌岌可危。時任浙江省省長的黃紹■,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幫助下,贊同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決定在龍泉、遂昌、云和三縣建立浙江的抗日根據地,選派有愛國熱情、年輕有為者任縣長,巽澤被任命為龍泉縣縣長,時年28歲,是當時最年輕的縣長。
1938年1月,滿懷愛國熱情的他,帶同合作界一批青年同事,并通過徐由整邀請部分共產黨員同赴龍泉工作,當時到龍泉工作的共產黨員有邵荃麟、王朝聞、張三揚、舒文等。在龍泉,為適應抗戰形勢的需要,他改革了舊縣政府的許多陋規,如增設政治工作指導室(簡稱政工室)、戰事政治工作隊(簡稱政工隊)等部門。這些重要部門都由中共黨員負責,開展宣傳抗日救國活動,如辦起圖書室、閱覽室,其中陳列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斯諾的《西行漫記》等進步書刊,供大家閱讀,后雖被查禁,私下傳閱的人仍不少。還成立歌詠隊、話劇團,開辟宣傳欄,教唱抗戰歌曲,演出活報劇等。通過一系列活動,民眾的抗日熱情日益高漲,隨處都可聽到“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等歌聲;街頭活報劇《放下你的鞭子》的演出,激發起了群眾對日寇和賣國賊的仇恨,增強了民眾對抗戰必勝的信心和決心。
在中共黨員的幫助下,巽澤還采取種種措施,如實行“二五減租”,減輕農民的負擔;以平抑糧價,幫助群眾組織生產等辦法解決人民生活困難。在征兵方面,不采用抓壯丁的方式,而是通過宣傳,動員青年自覺報名。在逢年過節時,邀請烈軍屬到縣政府聚餐,親自向他們敬酒,形成“烈軍屬光榮”的風氣,因此青年參軍踴躍。
龍泉抗日進步活動的蓬勃發展,得到進步人士的贊許,有人稱龍泉為“紅色的龍泉”,唐巽澤為“紅色縣長”,名記者曹聚仁在一篇報道中稱龍泉為“東南的堪察加”。與此同時也引起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極大恐慌,他們散布謠言說:“龍泉已成為‘蘇區’。”當地的地主豪紳們也因巽澤的各種措施侵害了他們的利益,對他恨之入骨,他們組織了“吃唐會”,以誣告、陷害等手段妄圖趕走唐巽澤和共產黨。他們先利用美人計把收發室的工作人員拉下水,要他銷毀往來文件,致使上下公文往來受阻,直到上級追查縣長責任時,才發現這是土豪劣紳們設下的陷阱,幸虧收發人員只將文件藏在地板下,未予銷毀。真相終于大白,但國民黨黨部仍借此事提出要改組縣政府。
土豪劣紳們一計未成,又生一計,他們利用縣自衛隊隊長吳玉坤喜歡吃喝嫖賭,以請吃、請賭把吳玉坤拉下水,吳輸光了積蓄、餉銀,最后竟盜賣槍支,土豪劣紳們抓住這點,威逼利誘,唆使他上山為匪。當吳帶領十幾個士兵攜械上山后,豪紳們立即散布說“唐巽澤的親信攜帶槍支投了共產黨”。一時間謠言紛起,國民黨黨部抓住這一機會要嚴辦唐巽澤,在這危急時刻,龍泉的共產黨組織動員所有黨員和政工隊員隨同縣政府追捕部隊一起上山,開展政治喊話,吳手下的士兵紛紛攜械歸來,最后吳被抓回槍決。事實搞清,但國民黨仍把“唐巽澤的親信自衛隊長吳玉坤攜帶槍支投奔共產黨,在多方的壓力下吳玉坤被追回槍決”作為“事實”記入檔案卷宗中。這也就是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貼出“揪出歷史反革命唐巽澤”的大字報的依據。
1939年,國民黨在抗日前線節節敗退,但反共氣焰更為囂張,龍泉的共產黨員處境日益惡化,為避免損失,黨組織將黨員陸續調走,有的去了抗日前線,有的到了革命根據地等,在黨員都走了以后,巽澤也被調回建設廳任合作管理處副處長。巽澤雖離開了龍泉,但當地老百姓卻一直把他銘記在心。記得1981年我參加省政協副主席彭瑞林組織的一次學習考察活動,在龍泉學習考察時,有幾位七八十歲的老人知道我是唐巽澤的妻子,便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開,嘴里不住地說:“唐縣長好、唐縣長好!”他們的舉動深深感動了我,使我對巽澤在龍泉的活動有了更多的了解。
被逼在滬尋求新的發展
1946年9月,我從遵義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復旦大學新設的合作系。上課時,經常聽到老師介紹浙江的合作事業,并稱贊浙江合作界的唐巽澤是個人才。老師多次的提及,給我留下較深的印象。次年暑假,我被分配到杭州在浙江省合作處下屬的一個單位實習,唐巽澤是合作管理處處長,因是校友,他對我比較關心,因此我與巽澤有了較多的接觸。當時因杭州公務員罷工,巽澤被國民黨省黨部懷疑為策劃者,對其施加壓力,巽澤被迫離杭去滬謀生。在上海的老同學的幫助下,他掛牌為律師,同時到復旦合作系兼課。
巽澤在復旦合作系講授的是合作運動史,他以社會發展史的觀點來講課,由于他的學識,他的口才,以及深入淺出、生動的講解,深得同學們的歡迎。他喜歡接近群眾,同學們也喜歡他,故在課前課后總有不少同學圍繞著他談論一些問題。他來上海后,使我對巽澤有了更深的了解,1948年我們終于結為伴侶。
在上海,巽澤有很多朋友,其中有共產黨員、民主人士以及從事其他職業的。他與他們接觸頻繁,通過黨員,他了解了共產黨在解放區的方針政策;在與民主人士的接觸中,他參加了民主革命同盟(又稱“小民革”);在與其他人士的交往中,他根據黨的方針政策采取適當的方式進行宣傳,特別是在1948年,解放軍南下勢如破竹,上海許多工商業者由于對黨的政策不了解,聽信謠言,人心惶惶,有想逃香港的,有準備抽資的,巽澤根據黨的政策以友情規勸他們,終于使他們以觀望的態度留在上海。
為勞軍工作不辭辛勞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我們親眼目睹解放軍軍紀嚴明,不進民居而露宿在馬路上,深受感動。“七一”前,巽澤接到杭州市軍管會的通知,邀請他參加“七一”民主人士座談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馬寅初、李士豪、姜震中、蔡一鳴等,會議由軍管會主任譚震林主持。巽澤在會上率先發言,贊揚共產黨的城市政策,并對恢復和發展生產提出了建議,引起譚震林等領導的注意。接著馬寅初又在會上贊揚了巽澤在龍泉的業績,稱他為“年輕有為,廉潔的縣長”。會后譚震林主席邀請巽澤回浙工作,他欣然同意。
回杭后,巽澤即參加由馬寅初主持的杭州慰勞解放軍總會的工作,擔任副組長并負責籌款事務。為了解放全中國,解放軍南下的任務很緊,勞軍工作非常緊張,他經常工作至深夜才回家。杭州解放不久,國民黨潛伏的特務不甘心失敗,妄圖以恫嚇、威脅,甚至寄附有子彈的信件,企圖阻止和破壞勞軍工作,但巽澤不為所動,堅持工作到勞軍總會結束。
在勞軍籌款期間,他與杭州工商界中的上層人士有了較多的接觸。7月,杭州市組織部分工商界代表人士赴華北、東北參觀訪問,巽澤任團長,在經過北京時,參加了民建。途中,他與工商業者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交往。回杭不久,就擔任了杭州市工商聯籌委會的副主委,負責宣教和日常工作,從此,與工商界結下了不解之緣。
籌建杭州民建,貫徹黨的團結教育改造方針
1950年6月,巽澤根據民建總會指示,負責籌建民建杭州分會。在籌建過程中,他通過工商聯的工作,動員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參加民建。當時工商業者對參加民建心存顧慮,主要是擔心萬一國民黨回來要吃苦頭,但在他的動員下,很多人還是參加了,我當時在做工商業者家屬的工作,也參加了民建。一年后,分會成立,會員人數已達數十人。
解放初期,巽澤根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對工商業者進行愛國守法教育,組織學習《共同綱領》、《過渡時期總路線》等。但由于工商業者認為共產黨要消滅階級,一定會利用各種機會來沒收資本家的財產,因此當“五反運動”開始,要工商業者交代“五毒”行為時,很多人怕交代多了今后拿不出,交代少了過不了關,顧慮重重,有人湊足資產數,作為交代的數字,認為政府把資產拿去,自己就可以摘掉資本家的帽子,不必再挨斗挨批。這種思想在工商業者中引起共鳴,思想一度比較混亂。巽澤發覺這一問題后,利用大會小會,反復講清黨的政策,使工商業者的思想逐步得到澄清。當時,有不少工商業者擔心被評為違法戶,但由于思想工作深入,嚴格按政策辦事,極大部分都被評為完全守法戶,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從此工商業者對黨的政策開始有所認識。他們說:“唐主委作報告深入淺出,聯系實際,針對我們的問題啟發性強,幫助我們解決了不少思想問題,掃清了思想障礙。”因此,凡民建、工商聯開大會,只要聽說是唐主委作報告,幾百人的禮堂就座無虛席。
1952年,巽澤參加第二批赴朝慰問團。在朝鮮,他接觸到的志愿軍都很年輕,并且憨掬可愛,對從祖國來的親人,他們給以熱情細致的照顧。在慰問中,他深深地被志愿軍戰士的英勇事跡和中朝人民血肉相連的情景所感動。他在回國后的傳達匯報中,以生動而充滿激情的敘述,報告了他在朝鮮戰場上的所見所聞,特別是在表達志愿軍戰士“為了祖國,前進!”的呼喚時,臺下的聽眾無不為志愿軍戰士為了保家衛國,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大無畏精神而動容,堅信抗美援朝必勝。
巽澤非常重視群眾工作,只要稍有空就會到基層去找幾個會員座談,傾聽他們對形勢、政策以及工作的看法和意見,他不僅身體力行,要求干部也如此,他說:“我們做群眾工作,不接近他們,不了解他們的想法,如何做好工作。”在他的帶動下,民建的干部和會員之間的感情是非常融洽的。省、市民建機關的干部不多,會員卻不少,每個干部至少聯系一個支部,每周一次支部組織生活,會前需開支委會,必要時還要到企業了解情況,為了適合會員的時間,支部組織生活都安排在晚上,其他許多會議也基本上都在晚上,因此會機關經常是燈火通明。干部不僅白天晚上需要工作,還要利用星期天到會員家中家訪。機關干部都習慣了這種生活,會員也樂于到會里來拉拉家常,談談思想,提提意見和建議,并及時將情況綜合報黨委部門,得到黨委部門重視。
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開始后不久,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自由民主黨要召開代表大會,邀請民建中央派代表參加。民建中央決定由副主委胡厥文出席,并要浙江的唐巽澤和天津的唐寶心陪同前往。巽澤是整風領導小組成員之一,接到這一通知后感到左右為難,去民主德國是民建中央對他的信任,但又擔心會影響“整風反右”工作。省委統戰部知道后,認為去民主德國的任務也是統戰工作,答應替他安排好工作,讓他安心去。到了民主德國后,可能由于路途疲勞,他發高燒,但仍堅持工作,當民主德國朋友與他握手時,才發現他在發燒,一定要他去醫院看病,當他瘦骨嶙峋的身軀暴露在醫師和民主德國朋友們的面前時,他們無不驚訝萬分,慨嘆說:“像唐這樣的人還在工作,真是不可思議。”他們無不感佩中國人的刻苦頑強精神。
巽澤對自我改造抓得很緊,平時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深入研究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對家人也不放松,一再告誡:“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放松改造就容易犯錯誤。”他的生活比較儉樸,上班、開會只要離家較近,他都不坐車,有人為他叫車,他說:“步行能鍛煉身體,步行慣了,沒有車也行。”在20世紀60年代的3年自然災害時,政府號召大種大養,我們利用屋前的一小塊園地,種上番茄和南瓜,收獲雖不多,讓孩子們也有了學習勞動的機會。
巽澤不僅在民建、工商聯擔任領導職務,他還是杭州市政府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省水產廳廳長及省政協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由于擔任的職務多,聯系的群眾面亦廣,為了無愧于擔任的職務,他總是盡可能地抽出更多的時間來做好各項工作。政協是各界人士和知識分子云集的地方,在知識分子中由于家庭出身不同,接受教育的途徑各異,因此對接受黨的領導和思想改造的認識,也有很大差異,擁護的有,抵觸的也不少,觀望的更多。為了端正大家的認識和態度,巽澤在政協的支持下,組織知識分子根據各個時期的中心展開辯論,在辯論中明辨是非,在自我教育中推動自我改造。知識分子對這種比較寬松又能夠敞開思想的辯論感到得益不少,很多人的態度逐步有了轉變。
由于巽澤過去的經歷,在浙江的愛國人士中彼此都有所了解,雖然各人經歷不同,但相互間比較信任,各項工作容易協調,為統一戰線工作的順利進行,發揮了作用。
冤假錯案終于平反昭雪
1966年5月,電臺廣播了“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消息,不久北京市委改組,巽澤有些震驚,其時他因心臟病休息在家。接著我家被抄,他被勒令掃街,這些他都不在意,認為運動難免有過激的行為。當宣布挖出“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并說這是統治17年的黑線時,他預感到一場政治風暴即將來臨,擔心身體是否能經受得住這場風暴的沖擊,我也為他而擔憂。
運動很快席卷了全國,民建、工商聯的造反派貼出了“揪出歷史反革命分子唐巽澤”的大字報,并聲稱要剝去他的“紅色縣長”及左派的兩張畫皮,在這正反錯位、是非顛倒的歲月里,他感到有口難辯。被勒令交代的同時,外調人員接踵而至,由于他過去接觸的人多,加上年代久遠,許多人和事已想不起、記不清,不能滿足外調人員的要求,因此受挨打、遭辱罵,幾成家常便飯,但他說:“我必須實事求是,我不能害人。”
在無休止的寫交代、寫外調材料的重壓下,本來就瘦弱的他,更顯得骨瘦如柴。長期的失眠,安眠藥從2片增到8片。1968年8月,我隨單位去嘉興“雙搶”,孩子們又有各自的活動,家中無人照料,他的身心遭受了雙重摧殘,尊嚴喪失殆盡,心力交瘁,高燒不退,終于無力承受,被逼含冤而死。但即使在他決心離世之際,還念念不忘教導家人“要聽黨的話,走社會主義道路”。
1978年9月19日在杭州舉行“唐巽澤先生追悼會”,為他恢復名譽。追悼會由省政協主席毛齊華主持,省政協副主席、中共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余紀一致悼詞。
悼詞中說:“在抗日戰爭初期,他擁護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贊同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在抗日戰爭期間做了有益的工作。全國解放后,他擁護、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周總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熱愛社會主義祖國,他努力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關心國家大事,歷次運動都積極響應,堅決貫徹執行我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多年來,他在我省工商界以及其他愛國人士中,做了大量工作。為鞏固和發展我省統一戰線工作貢獻了力量,是一位長期與我黨密切合作共事的老朋友。”黨為巽澤平反昭雪,他可以安息了!巽澤走了,留下的卻是我們對他永久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