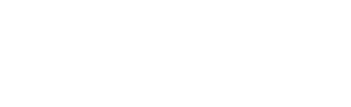回憶先父章乃器
發布時間:2010-05-12 17:34:09
|
作者: 章翼軍
章乃器(1896--1977),又名章埏,字子偉,浙江青田人。1945年發起組織民建,歷任民建理事、常務理事,民建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委員、常委,民建總會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第一屆中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政務院政務委員,編制委員會主任,財經委員會委員,糧食部部長。全國工商聯第一、二屆副主任委員。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二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教子艱苦從嚴
父親章乃器(1896--1977)是浙江青田人。我出生在上海,5歲時就離開父親,隨生母回到浙江遂昌祖父家中居住。15年后,我又重新回到上海,在父親身邊度過了難忘的4年。在我的印象中,父親是一位知名愛國人士,又是一位嚴父。
1936年11月23日,父親和沈鈞儒、鄒韜奮等“愛國七君子”被捕時我還年幼,正在遂昌縣妙高中心小學讀書。當老師告訴我這個消息時,我雖然還不大懂事,但知道父親是因愛國坐牢的,內心油然產生了敬意。當時學校老師教我們唱抗日歌曲,演出愛國的話劇,我非常喜愛,并積極參加。
10年后,我又回到上海。1946年6月,一天,繼母楊美真帶我去龍華機場迎接父親(自重慶飛上海),父子才重新見了面。同機到達的還有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夫婦。第二天報載:“名經濟學家章乃器氏昨自渝抵滬。”
我們家住在上海膠州路一條普通的弄堂里,兩室一廳的公寓房,簡單的擺設。父親每天到外灘的公司上班,坐的是一位朋友借給的汽車。后來,姑母把她的老掉牙的汽車借給父親使用。
我從浙江鄉下出來,原以為可以過一下舒適的生活了,誰知事與愿違。我穿的是父親的舊中山服和從舊貨攤上買來的舊西裝,有些同學到校都有自備車或小車接送,手上戴的是名牌手表。我呢,什么也沒有。當時我很生氣,對父親很有意見。我覺得在同學面前低人一頭,在學校里抬不起頭來。現在回想起來,父親在生活上對我的嚴格要求,是對我真正的愛護。他常常對我說:“上海這個地方是一個大染缸。一個人的墮落往往是從生活上貪圖享受開始的。你是一個學生,經濟上還不能自立,生活上艱苦點好。”當時,繼母對我們的生活作了適當的安排。
在上海、香港從事愛國民主運動
父親在上海一面辦企業,一面從事民主運動,并在滬江大學商學院任教。他的公開職務是上川企業公司經理。工作是很忙的。每天除了上班,還要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參與組織各界代表赴京請愿,反對國民黨召開“國大”、通過“憲法”等。中國民主建國會所發表的聲明、談話,大都出自父親的手筆。我清楚地記得,著名教育家、救國會主要領導人之一陶行知先生逝世時,在江灣舉行追悼會,父親應邀參加,繼母和我陪同前往,途遇國民黨士兵搗亂,被迫中途折回,沒有去成,真是遺憾極了。父親還常常應邀到各處講演。一次滬江大學進步學生請父親作形勢報告,我陪同父親一塊去,兩個小時的報告,內容生動,分析透徹,講話經常被掌聲打斷。
1946年冬,上海成立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父親是會員之一。他和許多著名學者如周谷城、馬寅初、張志讓、楚圖南、翦伯贊、葉圣陶、蔡尚思等一起積極參加了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反對法西斯專政、反對簽訂賣國條約和支持罷工、罷課、罷教的民主運動。
父親經常參加上海工商界的活動,如各種聚餐會,我在滬江大學上學是住校的,平常很少回家,節假日全家才能碰在一起吃飯。父親的食欲很好,吃飯總是大口大口地吃菜,不管吃什么,他都吃得津津有味,從不挑食。因此,他的身體很好。吃飯時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不許隨便說話,據說這樣合乎衛生。晚飯后,父親總是挑燈夜讀,閱讀文件和報紙,特別是從解放區來的消息,或是撰寫文章,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時,還要會見來訪的客人,包括外國朋友。他的英語主要是靠自學,能寫、能讀、能聽、能講,會話時應付自如,對答如流。
我后來才知道,父親從重慶一回到上海,就受到國民黨特工人員的監視。上海靜安寺警察分局局長廖某,是浙江青田人,和父親是同鄉,也是遠親。廖是軍統戴笠手下的人。一天晚上,廖等2人來訪,當時我也在場。從談話中得知,他們知道父親要到臺灣去視察(打算經營糖業公司),竟主動提出來要“陪同”父親一起去,名為“保護”,實為監視。
由于形勢的發展和工作的需要,父親和繼母先后離滬去香港。上川公司副經理黃玠然一家搬來我們家住。公司的職員也隨同一起來搭伙。黃老是老共產黨員,早在重慶時,周恩來副主席就派他到上川實業公司協助父親工作,一直到上海、香港。解放后,我才知道黃伯母也是地下黨員。
父親到香港后與李葆和合作創辦了港九地產公司,經營地產業務。又投資昆侖影片公司,攝制《一江春水向東流》影片上下集。同時,民主建國會總會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定,由章乃器、孫起孟、田鐘靈、嚴希純、何民麟、林大琪、徐崇林等7人負責籌備港九分會,以父親為召集人。
1948年,中國共產黨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民建會在香港的理監事當即公開表示響應。民建總會并指定父親和孫起孟為駐港代表,與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保持聯系。
同年12月4日,民建與民革、民盟等民主黨派聯合發表《為保護產業,保障人權告國內同胞及各國僑民書》。聲明“希望所有未解放城市同胞以及各國僑民,都安心繼續自己的事業和工作。而且希望大家更進一步地團結起來,為保護自己的產業和保障自己的人權而奮斗,堅決抵抗南京獨裁政權的一切破壞產業和迫害人民的暴行。”與此同時,民建總會決定推派父親和孫起孟、施復亮為代表,到北平參加籌備新政協的工作。
當時,香港是一個自由港,情況極為復雜,各種政治力量都在那里活動。民主黨派的工作處于半秘密狀態。我家住在英皇道,與馬敘倫、金仲華、薩空了、邵荃麟等都是近鄰。據杜宣同志回憶:“當時我們的住所都受到特務的監視。在街道拐彎的電線柱子下,就是一個監視站。無論天晴下雨,總有一個特務站在那兒。”處境同樣是險惡的。但是由于中共地下工作者機智勇敢,精心安排,終于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及家屬一批批地安全送到解放區。1948年12月,父親喬裝成商人,坐輪船北上,從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登陸,到達沈陽轉赴北平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的。
在歡慶解放的日子里
父親在東北解放區參觀了沈陽、哈爾濱等地,目睹解放區在短期內取得的巨大成就,贊不絕口。1949年3月,他到北平不久,就寫了一篇文章《人民的東北》,滿腔熱情地描述了他在東北各地參觀的所見所聞。他坦率地承認,過去對新華社報道有關解放區的政治經濟情況,抱有一定程度的懷疑,而在實地參觀之后,不僅認識到自己過去的懷疑毫無根據,而且覺得新聞報道還遠遠地落在事實之后。他深感新生的事物太豐富,人民的愉快心情和社會的蓬勃景象,絕非一般的文章所能描繪。他以欽佩的心情熱情地寫道:“對于這些,我近來常感到散文無用,而必須用詩歌來表達。因此,一向不喜歡詩歌的我,現在都想學寫詩歌,以抒發胸中勃發的詩意。”這是父親出自內心深處的肺腑之言。
同年4月初,我和妹妹章畹從香港到了北平。當時,父親、繼母和許多民主人士及其家屬都住在六國飯店,而父親讓我們住在他的老朋友吳羹梅伯伯家里,這樣可以減輕國家的一些負擔。同時他又鼓勵我們早日參加革命工作。他對我和妹妹說:“國家現在需要大批干部,你們是否可以先到‘革大’學習幾個月,學點革命理論,提高思想認識,爭取早日工作。”經過考慮,我和章畹同時進入“革大”學習,繼母也到“革大”高級班學習。臨近畢業,父親又和我談話,鼓勵我們服從組織分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鍛煉成長。我于1949年8月分配到綏遠(今內蒙古),至今已有38個春秋了。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父親作為民主建國會的代表出席會議,并在會上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他說:“參加了這個歷史性盛會,使得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新民主主義的偉大,更親切地體驗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確。會議的成就證明了中國在中共的領導之下,遵循著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前進,一定可以達到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境界。”
在逆境中度過晚年
父親是一個有開拓精神的人。黨信任他,委以重任,曾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糧食部部長等職。他沒有辜負黨對他的重托,兢兢業業地埋頭工作。后來,由于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父親被錯劃為右派。但他堅信自己沒有反黨,問題總會澄清。他仍孜孜不倦地學習、努力鍛煉身體。他曾說:“我的問題弄清后,還要為黨工作10年。”“文化大革命”中父親受盡了磨難,是周恩來總理保護了他,才免于一死。
1975年4月,父親被摘掉右派帽子,陳云同志找他談話,傳達中共中央對他的關懷,打算給他作適當的安排。不幸的是,父親的身體已經不允許他為人民再做工作了。1977年5月13日,父親病逝于北京醫院,享年80歲。
1980年7月,父親被錯劃右派的問題終于得到改正。1982年5月14日,在父親逝世5周年的時候,父親的骨灰被移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人民日報》在頭版四條作了報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聯播節目中作了廣播,對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肯定的評價。父親如地下有知,九泉之下也當能瞑目了。
教子艱苦從嚴
父親章乃器(1896--1977)是浙江青田人。我出生在上海,5歲時就離開父親,隨生母回到浙江遂昌祖父家中居住。15年后,我又重新回到上海,在父親身邊度過了難忘的4年。在我的印象中,父親是一位知名愛國人士,又是一位嚴父。
1936年11月23日,父親和沈鈞儒、鄒韜奮等“愛國七君子”被捕時我還年幼,正在遂昌縣妙高中心小學讀書。當老師告訴我這個消息時,我雖然還不大懂事,但知道父親是因愛國坐牢的,內心油然產生了敬意。當時學校老師教我們唱抗日歌曲,演出愛國的話劇,我非常喜愛,并積極參加。
10年后,我又回到上海。1946年6月,一天,繼母楊美真帶我去龍華機場迎接父親(自重慶飛上海),父子才重新見了面。同機到達的還有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夫婦。第二天報載:“名經濟學家章乃器氏昨自渝抵滬。”
我們家住在上海膠州路一條普通的弄堂里,兩室一廳的公寓房,簡單的擺設。父親每天到外灘的公司上班,坐的是一位朋友借給的汽車。后來,姑母把她的老掉牙的汽車借給父親使用。
我從浙江鄉下出來,原以為可以過一下舒適的生活了,誰知事與愿違。我穿的是父親的舊中山服和從舊貨攤上買來的舊西裝,有些同學到校都有自備車或小車接送,手上戴的是名牌手表。我呢,什么也沒有。當時我很生氣,對父親很有意見。我覺得在同學面前低人一頭,在學校里抬不起頭來。現在回想起來,父親在生活上對我的嚴格要求,是對我真正的愛護。他常常對我說:“上海這個地方是一個大染缸。一個人的墮落往往是從生活上貪圖享受開始的。你是一個學生,經濟上還不能自立,生活上艱苦點好。”當時,繼母對我們的生活作了適當的安排。
在上海、香港從事愛國民主運動
父親在上海一面辦企業,一面從事民主運動,并在滬江大學商學院任教。他的公開職務是上川企業公司經理。工作是很忙的。每天除了上班,還要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參與組織各界代表赴京請愿,反對國民黨召開“國大”、通過“憲法”等。中國民主建國會所發表的聲明、談話,大都出自父親的手筆。我清楚地記得,著名教育家、救國會主要領導人之一陶行知先生逝世時,在江灣舉行追悼會,父親應邀參加,繼母和我陪同前往,途遇國民黨士兵搗亂,被迫中途折回,沒有去成,真是遺憾極了。父親還常常應邀到各處講演。一次滬江大學進步學生請父親作形勢報告,我陪同父親一塊去,兩個小時的報告,內容生動,分析透徹,講話經常被掌聲打斷。
1946年冬,上海成立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父親是會員之一。他和許多著名學者如周谷城、馬寅初、張志讓、楚圖南、翦伯贊、葉圣陶、蔡尚思等一起積極參加了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反對法西斯專政、反對簽訂賣國條約和支持罷工、罷課、罷教的民主運動。
父親經常參加上海工商界的活動,如各種聚餐會,我在滬江大學上學是住校的,平常很少回家,節假日全家才能碰在一起吃飯。父親的食欲很好,吃飯總是大口大口地吃菜,不管吃什么,他都吃得津津有味,從不挑食。因此,他的身體很好。吃飯時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不許隨便說話,據說這樣合乎衛生。晚飯后,父親總是挑燈夜讀,閱讀文件和報紙,特別是從解放區來的消息,或是撰寫文章,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時,還要會見來訪的客人,包括外國朋友。他的英語主要是靠自學,能寫、能讀、能聽、能講,會話時應付自如,對答如流。
我后來才知道,父親從重慶一回到上海,就受到國民黨特工人員的監視。上海靜安寺警察分局局長廖某,是浙江青田人,和父親是同鄉,也是遠親。廖是軍統戴笠手下的人。一天晚上,廖等2人來訪,當時我也在場。從談話中得知,他們知道父親要到臺灣去視察(打算經營糖業公司),竟主動提出來要“陪同”父親一起去,名為“保護”,實為監視。
由于形勢的發展和工作的需要,父親和繼母先后離滬去香港。上川公司副經理黃玠然一家搬來我們家住。公司的職員也隨同一起來搭伙。黃老是老共產黨員,早在重慶時,周恩來副主席就派他到上川實業公司協助父親工作,一直到上海、香港。解放后,我才知道黃伯母也是地下黨員。
父親到香港后與李葆和合作創辦了港九地產公司,經營地產業務。又投資昆侖影片公司,攝制《一江春水向東流》影片上下集。同時,民主建國會總會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定,由章乃器、孫起孟、田鐘靈、嚴希純、何民麟、林大琪、徐崇林等7人負責籌備港九分會,以父親為召集人。
1948年,中國共產黨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民建會在香港的理監事當即公開表示響應。民建總會并指定父親和孫起孟為駐港代表,與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保持聯系。
同年12月4日,民建與民革、民盟等民主黨派聯合發表《為保護產業,保障人權告國內同胞及各國僑民書》。聲明“希望所有未解放城市同胞以及各國僑民,都安心繼續自己的事業和工作。而且希望大家更進一步地團結起來,為保護自己的產業和保障自己的人權而奮斗,堅決抵抗南京獨裁政權的一切破壞產業和迫害人民的暴行。”與此同時,民建總會決定推派父親和孫起孟、施復亮為代表,到北平參加籌備新政協的工作。
當時,香港是一個自由港,情況極為復雜,各種政治力量都在那里活動。民主黨派的工作處于半秘密狀態。我家住在英皇道,與馬敘倫、金仲華、薩空了、邵荃麟等都是近鄰。據杜宣同志回憶:“當時我們的住所都受到特務的監視。在街道拐彎的電線柱子下,就是一個監視站。無論天晴下雨,總有一個特務站在那兒。”處境同樣是險惡的。但是由于中共地下工作者機智勇敢,精心安排,終于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及家屬一批批地安全送到解放區。1948年12月,父親喬裝成商人,坐輪船北上,從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登陸,到達沈陽轉赴北平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的。
在歡慶解放的日子里
父親在東北解放區參觀了沈陽、哈爾濱等地,目睹解放區在短期內取得的巨大成就,贊不絕口。1949年3月,他到北平不久,就寫了一篇文章《人民的東北》,滿腔熱情地描述了他在東北各地參觀的所見所聞。他坦率地承認,過去對新華社報道有關解放區的政治經濟情況,抱有一定程度的懷疑,而在實地參觀之后,不僅認識到自己過去的懷疑毫無根據,而且覺得新聞報道還遠遠地落在事實之后。他深感新生的事物太豐富,人民的愉快心情和社會的蓬勃景象,絕非一般的文章所能描繪。他以欽佩的心情熱情地寫道:“對于這些,我近來常感到散文無用,而必須用詩歌來表達。因此,一向不喜歡詩歌的我,現在都想學寫詩歌,以抒發胸中勃發的詩意。”這是父親出自內心深處的肺腑之言。
同年4月初,我和妹妹章畹從香港到了北平。當時,父親、繼母和許多民主人士及其家屬都住在六國飯店,而父親讓我們住在他的老朋友吳羹梅伯伯家里,這樣可以減輕國家的一些負擔。同時他又鼓勵我們早日參加革命工作。他對我和妹妹說:“國家現在需要大批干部,你們是否可以先到‘革大’學習幾個月,學點革命理論,提高思想認識,爭取早日工作。”經過考慮,我和章畹同時進入“革大”學習,繼母也到“革大”高級班學習。臨近畢業,父親又和我談話,鼓勵我們服從組織分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鍛煉成長。我于1949年8月分配到綏遠(今內蒙古),至今已有38個春秋了。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父親作為民主建國會的代表出席會議,并在會上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他說:“參加了這個歷史性盛會,使得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新民主主義的偉大,更親切地體驗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確。會議的成就證明了中國在中共的領導之下,遵循著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前進,一定可以達到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境界。”
在逆境中度過晚年
父親是一個有開拓精神的人。黨信任他,委以重任,曾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糧食部部長等職。他沒有辜負黨對他的重托,兢兢業業地埋頭工作。后來,由于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父親被錯劃為右派。但他堅信自己沒有反黨,問題總會澄清。他仍孜孜不倦地學習、努力鍛煉身體。他曾說:“我的問題弄清后,還要為黨工作10年。”“文化大革命”中父親受盡了磨難,是周恩來總理保護了他,才免于一死。
1975年4月,父親被摘掉右派帽子,陳云同志找他談話,傳達中共中央對他的關懷,打算給他作適當的安排。不幸的是,父親的身體已經不允許他為人民再做工作了。1977年5月13日,父親病逝于北京醫院,享年80歲。
1980年7月,父親被錯劃右派的問題終于得到改正。1982年5月14日,在父親逝世5周年的時候,父親的骨灰被移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人民日報》在頭版四條作了報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聯播節目中作了廣播,對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肯定的評價。父親如地下有知,九泉之下也當能瞑目了。